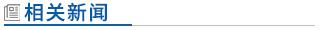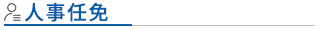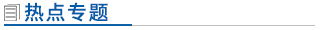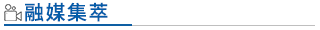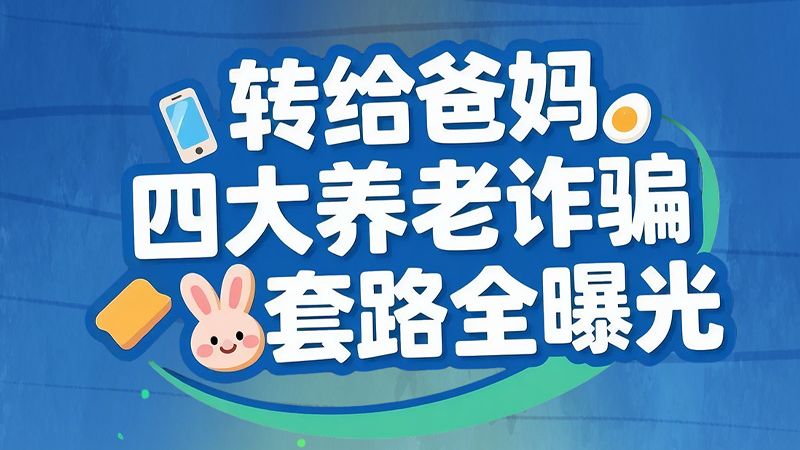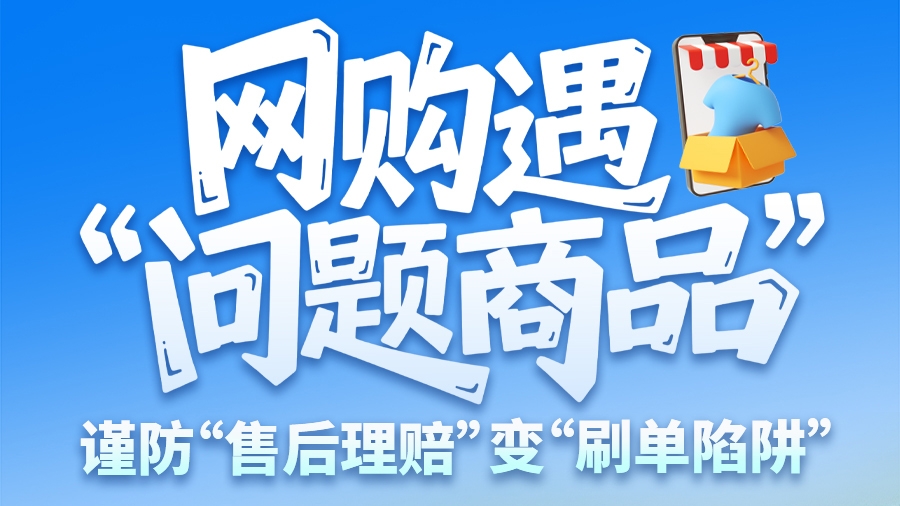楊建仁
金秋時節,大美敦煌。第八屆絲綢之路(敦煌)國際文化博覽會開幕前夕,由著名作家葉舟作詞,知名青年音樂人段興華作曲,奔流新聞制作并聯合甘肅國際傳播中心出品發布的一首MV《敦煌頌》,在各大網絡平臺廣為傳播,瞬間掀起了一股洶涌澎湃的“敦煌頌”熱潮。
第八屆絲綢之路(敦煌)國際文化博覽會開幕式當天晚上,葉舟從敦煌發來一張深夜拍攝的照片,在一束強光的照射下,由賈平凹書寫,雕刻在一塊質地厚重、紋理清晰的石頭上的10個金色大字:“敦煌葉舟文學創作基地”,金光閃閃,熠熠生輝,給人一種莊重的偉岸和肅穆的力量。第二天早晨6點剛過,葉舟又發來當天《人民日報》大地副刊頭條發表他的文章《〈敦煌頌〉只有八句》。我立馬回復:“天時地利人和。”我想表達的意思就是,《敦煌頌》并不長,只有短短的八句:“一沙一葉一佛像,一山一泉一故鄉。一窟一墻一壇場,一筆一畫一頌唱。一卷一紙一蒼茫,一秋一春一照亮。一天一地一念想,一世一生一敦煌。”這首看似信手拈來的八句歌詞,不是葉舟刻意撰寫的應景之作,也不是心血來潮的急就之章,而是被敦煌文化喂養了30多年后,自然盛放的一朵最靜美的蓮花。
敦煌之于葉舟,就是一生魂牽夢縈的思念,就是一世不棄不離的陪侍,就是一命所系所懸的天空,就是一輩子躬身叩拜的大地。20世紀90年代,大學畢業不久的葉舟,利用業余時間,身背行囊,孤身一人行走在祁連山下的河西四郡和兩關之間,一次次觸摸戈壁、沙漠、胡楊、綠洲的心靈褶皺,一遍遍傾聽風沙、飛雪、駝鈴、馬嘶的酣暢交響,終于在遼闊而神圣的敦煌,找到了他安妥靈魂的歸宿。于是,他撲下身子,像淘金者一樣沒日沒夜地,撈取著散落在泥沙中的閃光顆粒。然后用整整10年的時間,鍛造出一部名叫《大敦煌》的詩文集。如今,這本詩文集仍在暢銷,“大敦煌”這三個字也成了常見詞匯。此后,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里,葉舟陸續寫出了《敦煌詩經》《藍色的敦煌》《敦煌本紀》《敦煌消息》等篇什,這些作品,大氣、健朗、清潔、明亮,拓寬了敦煌題材的新氣象,被文藝界稱之為“葉舟的敦煌現象”。
所以《敦煌頌》不是葉舟的偶然所得,引發熱度也不是巧合之遇,而是葉舟在用文字持續開窟造像時,用心用情描繪的最精美的一筆。雖然僅有八句,卻以極簡的文字,構建了一個宏大而深邃的文學和精神空間,其價值不僅在于語言的藝術性,更在于對敦煌文化內核的凝練表達與哲學思考。
全首歌詞連續使用24個“一”,形成獨特的計數詩風格。這種重復并非單調,而是通過“一”的疊加營造出莊嚴的儀式感和時空的延展性。每一處“一”既是具體事物的單元,也是無限時空的微小切片,暗示敦煌文化由無數個體細節匯聚而成,宏大而精微。歌詞選取的意象具有典型的文化符號特征,“沙”“葉”“山”“泉”等自然元素,指向敦煌的地理環境與生命本源;“佛像”“窟”“墻”“壇場”“筆”“畫”等人文符號,對應敦煌的宗教、藝術與歷史積淀;“蒼茫”“照亮”“念想”等抽象概念,則升華至精神層面。意象由實入虛,層層遞進,形成從物質到精神、從個體到永恒的立體畫面。每句采用“一X一X一X”的固定結構,工整對仗,朗朗上口,兼具民歌的復沓美與古典詩詞的格律感。這種形式上的統一性與敦煌文化中“秩序與和諧”的美學理念相契合,同時通過尾韻“像”“鄉”“場”“唱”“茫”“亮”“想”“煌”形成音韻閉環,象征文化的完整與傳承。歌詞將敦煌提升為跨越時空的文化坐標,呼喚人們對文化根脈的崇敬和守護。
《敦煌頌》的文學力量正源于其“極小形式”與“極大內涵”的矛盾統一:八句歌詞猶如一枚文化膠囊,濃縮了敦煌的物理空間、歷史層積與精神維度。它不僅是敦煌的頌歌,更是對所有人類文明的隱喻——文明由無數“一”構成,每一個“一”都值得敬畏,而正是這些微小單元的集合,照亮了人類存在的蒼茫與壯麗。

MV《敦煌頌》畫面
- 2025-09-28“聽見”敦煌壁畫的聲音——第四屆全球數字貿易博覽會見聞
- 2025-09-222025相約敦煌|從“護寶”到“傳揚”:敦煌研究院“典范”“高地”建設賦能敦煌文化出圈
- 2025-09-22奏響美美與共的華彩樂章——歷屆絲綢之路(敦煌)國際文化博覽會回顧
- 2025-09-22敦煌紀行:觸摸絲路文明的溫度

 西北角
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
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
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
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
今日頭條號